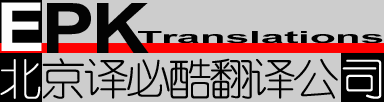谁翻译了可口可乐 财经时报 可口可乐,一直被认为是广告界翻译得最好的品牌名。不但保持了英文的音译,还比英文更有寓意。可口可乐四个字生动地暗示出了产品给消费者带来的感受——好喝、清爽、快乐——可口亦可乐。让消费者胃口十足,“挡不住的感觉”油然而生。
也正因如此,可乐逐渐成为饮品类的代名词和行业标准。据说,Pepsi在进入中国时也被迫翻译成“百事可乐”,而不是“百事”。
可乐是怎么创造出来的,大家可能早有耳闻,但它的命名过程,恐怕知道的人不多。
1886年,美国亚特兰大市的药剂师约翰·潘伯顿无意中创造了可口可乐。他的助手,会计员罗宾逊是一个古典书法家,他认为有两个大写字母C会很好看,因此用Coca-Cola作为这个奇异饮料的名称。
上世纪20年代,可口可乐已在上海生产,一开始翻译成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中文名字,叫“蝌蝌啃蜡”,被接受状况可想而知。于是可口可乐专门负责海外业务的出口公司,公开登报悬赏350英磅征求译名。当时身在英国的一位上海教授蒋彝,便以“可口可乐”四个字击败其他所有对手,拿走了奖金。
现在看来,可口可乐真是捡了个大便宜,350英镑的成本换来今天在中国数十亿的销售额。
据悉,蒋彝的后人还要将可口可乐告上法庭,把几十年来应得的利益讨回来。
有人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很多洋品牌进入中国都被我们翻译得恰倒好处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比如汽车中的Benze一开始翻译成了“笨死”,香港又叫“平治”,直到找到“奔驰”这个贴切的译名,才开始在中国大地奔驰如飞。
BMW翻译成宝马堪称神来之笔,至于被叫成“别摸我”,如同把CBD解释成中国北京大北窑的简称(CHINA BEIJING DABEIYAO)肯定让创始人不高兴。
翻译得舒服,就像给品牌挠了一个千年大痒。
成功的例子还有很多。
Walk man是索尼的发明。最初,索尼将Walk man定义为能够随身携带的播放机,后来,所有能够随身携带的播放机都被叫做Walk man.当然,这也是索尼的一个巨大的决策失误,他没有将Walk man当作品牌来做,而是当作产品来推广。
Citibank花旗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没有人能够追溯当时是谁翻译了这个名字,但它的来源很有意思。据花旗的一个朋友说,之所以要翻译成这个名字,只是因为它来自美国,而美国的国旗很花哨。
再来看一个反面例子,KPMG毕马威会计事务所。
“毕马威”这个名字虽然并没有太坏的联想,但在发音时,容易让中国人想起“齐天大圣”,容易让人误以为是乡镇企业。
KPMG在70年代末进入大陆市场,他的负责人要在工商部门注册,而不懂中文的他们就将公司三个创始人的名字,Peat,Marwick,Mitchell的谐音注册成了公司。当然,现在“毕马威”已经是国内著名的财务公司,另改一个中文名字会给企业带来无形的资产流失,对于“毕马威”来说,已经没有必要。
但如果在品牌联想越来越重要的今天,还有人起这样的名字,对企业将是致命的。
为企业和产品命名就像为自己的儿女取名字一样,父母非常注意孩子的名字有哪些寓意。
而对于企业来说,名称最好能够准确地向消费者传达品牌的内涵,使品牌更加精致、有亲和力。
一个好的名字应该承载一个品牌的内涵,传达品牌主张和承诺,帮助老板们打下一片疆土!(李光斗)
翻译质量和尴尬的出版界(一)
在新语丝看到了李继宏先生和施康强先生关于文学翻译的文章。我在此就翻译、翻译公司和出版本身发表一点看法,并非特地针对施、李两位的观点。
毋庸多言,出版相当数量的高品质图书是社会文化建设和传播的不可或缺的环节。然而中国大陆的图书出版现在是泥沙俱下,许多翻译作品尤其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这有着市场渠道和学术文化体系多方面的深层原因。我预计在未来的十年内,中国出版市场本身不会形成支持高品质图书的机制。而且由于学术标准的严重滑坡,公共资助的出版项目也缺少质量控制的机制。我相信许多人衷心的希望这种情况发生改变;在此不揣简陋,作一些探讨来抛砖引玉。
一、市场之为王
李文中对于目前图书发行的的数字应该是真实的。发行商吃掉利润的最大部分;出版社的经营状况不定;对于作者和译者来讲,除非是满足两个条件(一)拿得到合理提成的版税(二)畅销五万册以上,否则收入不会超出李文中的数目。
那么,出版业出售的是文化还是商品还是什么文化商品?李和施好像是代表了两类人的观点。施说:我们这个圈子的翻译家一天出产一千五百字。李说:我就是比你打字快!
笑话归笑话,翻译是有一定的门槛的。这在技术类书籍中更明显一些。市面上太多的计算机书籍翻译得惨不忍睹。要做好这类翻译,译者既需要懂技术、又要精通外语。但这类人可以轻易在美国作一个年薪六七万的程序员啊—哪一家出版商出得了这个水平上的薪水呢?就像施先生说的,外语高手有多个其他的比译书报酬高的选择。目前出版界的整体价位养不起一流人才。
撇开技术内容不谈,很多人不容易理解或无从评价外语的修养。其实除了个别的特例,一个人的外语只有在该语言的母语国家生活几年以上才可能达到足够的水平。因为语言中有太多生活和文化的内涵。许多人雾里看花又不求实证,谬误百出。我们在新语丝也看多了这种笑话。[1]
创作和翻译中的再创作也是需要相当的时间投入的。杜甫老人家这等大才,还要“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尽管如今写博客的人们大概很不屑于此了。
记得舟子也说过李“的英语在国内的人文学者中算不错的了”。我没有亲自看过,不作评论。我认为一个合格的译者,除了技术类的专业水平以外,在中外两种语言上都要有相当的素养。这类人才的成本是显然的,显然远在目前的稿酬水平之上的。所以出版商常常是滥竽充数,反正读者一般不会去对照原著的。技术类的书籍译坏了误人子弟?反正我们的教育系统误的还多了。文学类的也没有几个人会跟你较真儿的。
那么就市场来说,高质量的译著有没有竞争优势呢?换而言之,市场竞争会不会促进高质量译著的出现呢?
经典的自由市场经济据说是优胜劣汰的。那么优质的图书应该在市场中胜出。事实—远远复杂的多。
首先中国大陆的出版业离自由的市场经济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在按照世贸要求开放之前,所有的出版社还都是政府挂*单位,由新闻出版署卡着书号的咽喉。在一个政治敏感的特殊行业待久了,多数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离国际水平有相当的差距。要在这个市场里进化出优秀的人才,万里长征才开始了第一步。几家国际大出版社现在虎视眈眈;日后格局很难分晓。但是文化市场有很大的特殊性,恐怕中国的游戏还要按中国规则来玩。
其次图书之间的竞争与普通产品不同,不是简单的比质量比价格。如果一家出版社翻译了一本书,即使翻的很烂,很少会有人去重做同一本书。甚至同一题材的图书也尽量避免撞车。所以普通商品式的竞争是很弱的;可以竞争的是不同出版社的品牌。品牌不仅需要长期扎实的建设,而且需要社会性的文化基础来支持。即使有人去走这条苦路子,还要检验两个条件:(一)市场是否响应;(二)人才有无供应。
中国的大众出版市场没有成熟到自动选择质量的地步。几十年来的失败的教育体系严重影响了普通读者的思考阅读习惯。而在媒体上把持话语权的很多是同一体系出来的失败产品。结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依赖炒作的市场,一个余秋雨之类的赝品可以横行的市场。时代风气如此,也不是几年间变化的了的。总之,文艺类和自我提高类的畅销书对质量不敏感。
教育类图书肥水横流,但因为流入特定的口袋,和质量也没多少关系。
所以需要高质量的、市场能对图书质量产生响应的基本是技术和学术相关的非常细化的、销量有限的小区域。
在这些区域里,图书的质量能否提供足够的市场动力呢?图书的价格空间有限,短期内不可能与国际接轨。如果质量能促进利润,只有通过销量;而这个细化的市场里,销量有很低的上限。这样,这些图书不足以给利润分配中居于末位的作/译者提供像样子的经济动力。
人才也是一个瓶颈。我们已经看到目前的出版业在经济回报上很难支持一流的译者和作者。而编辑队伍同样有人才短缺的问题。在一个学术论文都难以控制质量的社会,有多少人才和机制来控制普通出版物的质量呢?
出版是一项文化事业。社会中需要学术界来传递知识和规则,需要众多的知识人士来沟通不同的社会群体;读者需要一个能从容读书的环境,需要独立自由的信息来选择。似乎我们的每一个环节都断开了?
所以我说中国出版市场在十年内不会形成支持高品质图书的机制。
施先生觉得质量很重要。我也认为质量很重要。然而当市场不能提供动力的时候,质量就无法进入正常的商业渠道。这只有在国民的经济和文化水平都达到了一定层次后才有可能。
[1] 再插一个笑话吧:昨天在PBS(美国公共电视台)看到一个喜剧短片,“我的名字是吴明”。话说一个中国小伙儿,转了一下地球仪,要把自己的前途赌在爱尔兰(其实是个不错的注,爱尔兰近年来经济大好);在图书馆找来资料,苦学了一通爱尔兰语。等到一路杀到都柏林后,才发现那里的人们都只说英语!